

就像“治大国若烹小鲜”一样,帝王将相没下过厨,小老百姓没做过主,闻听此言两厢都不知饭怎么吃了。
反之则不然。
“烹小鲜若治大国”,倘真能如此用功,粗茶淡饭即刻味同国宴。
“旅行就是一段人生”,在哪儿都是生活,何必死守一处。
一段人生结束,回来不标经纬度,不报菜名,能讲出几个不合群的亲身经历,也就不愧对那几张辛苦得来又被人撕剩的票根。
俄罗斯,认她的人连双头鹰上戴着三顶王冠都觉着是那么回事,烦她的人一想起来就问到底是谁把鸡脑袋竖着劈成两半的。
其实不用问,发言的人大多不在场。

到现在他老人家也不在了,我也病病殃殃不那么欢蹦乱跳了。只是有一天忽听一群苏联少年齐唱《莫斯科•北京》,引得一阵唏嘘,就想到他曾经认作老大哥的家里串串门。
请了俩星期假,用6天时间坐火车从北京跑到莫斯科。没什么值不值便宜贵的,旅行就是一段人生嘛,话不只是说给别人听的。

至于出国门前经过的东北城市,我的笔记中这么有一句:“小型磕头机还不依不饶蜂拥着吮吸大庆塌陷的乳房。”再配上图就不宜看了。况且在国际列上,这些家丑不表也罢。
最近几年客居山上的乡下,偶有故交造访,感叹我这种活法儿是他无法实现的梦想。我问为何,他反瞪我一眼回道我能跟你比么我有孩子,至今我也搞不清他是夸自己情感健全呢,还是骂我生理有毛病。
再看看无边落木中若隐若现的西伯利亚村落,有些人恐怕连梦都不敢做了。你信不信?哪天对机会我敢拿着照片找过去,住上一段儿。

俄罗斯有个绰号叫“战斗民族”,网上视频不是车祸斗殴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弄得人云亦云者不免心中发憷不大敢去,生怕入境第一件事就是被揍一顿。俄罗斯人自己可不这么看,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就经常棒喝俄罗斯人,骂他们像老娘们儿一样顺从。
我也去过芬兰,我知道北欧人五大三粗却生性腼腆,俄罗斯人也如是。你不跟他交往,他就显得很冷,交往上了,他可能比你还逗。比如一位列车员老兄,我这儿正背着老婆月台上偷拍美女呢,他在那儿扯着嗓门儿向姑娘告密,事后还冲我眨眨眼睛,把俩手捧在自己胸前比划人家哪儿美,你说这怎么话儿说的。

很多人对火车情有独钟,因为很多情节在飞机上根本来不及发生。
打年轻时候起,我那无才便是德的老婆不管是接站还是送,都是那么兴高采烈的,而我二十岁的诗句里就有“我的牙齿在送站月台上完成了一次次的碎裂”。
我国的绿皮车很慢,很脏,也没有两个人的包厢。我们的高铁又太快,快到陷在航空椅里的人们感觉不到昏昏欲睡的惆怅。

我和那位列车员老兄是香烟同好,每到一站,我就往那只背在后面的手里塞根烟卷儿,回到车上他就更起劲地用俄语为我们讲解下一站是哪儿,停多长时间。刚开始点头却听不懂,到第四天似乎就真明白了。
那位白衣老大姐是餐车唯一的厨师。一开始不知道,只是一次停靠,见她端着个小钢盆跳下月台跨过铁轨去喂一群流浪狗,遂生敬意。后来我每天都去餐车让这位厨娘做一顿饭,这双仁慈的手也确实是双烹调的好手。

在目不暇接的纷乱场景下,你发现手中的相机简直就是神器,因为它能为你那不大可靠的记忆提供精确的视觉备份。然而在极简的环境里,镜头似乎又变回那块充满噪点的失焦的玻璃。
贝加尔湖世界最深,连续几个小时隔窗眺望,那水天一色最终恍惚成了空空如也,眼前所有的景象凝结在一起竟然显示着无。这时候相机可算瞎了。我告诉你,凡是号称能拍到对岸的相机都没有去过苦海。这是我说的么。

有那么一刻,我看见白匪上将高尔察克身着旧海军制服端坐在我斜对面品一小杯咖啡。他从济马向东一站一站驶入接受处决的伊尔库斯克,而我的列车一路向西,时隔一百年,背道而驰中与他擦肩而过。这位捍卫双头鹰的白匪在被镰刀锤子枪决70年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侍应老兄走过来用英语提醒下一站是叶卡捷琳堡,再往西就是欧洲了。

西伯利亚的风景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色彩斑斓的森林,零星点缀的村舍,用肉眼也分辨不出贝加尔湖哪片儿最深。如果说到特别,那就是超过3000公里绵延不绝的这条风景线,实在是太长了。

这要是落在眼里没谁的美国人手里,肯定会把它大卸八块儿再车头朝天焊接起来以纪念苏联解体,他们干过类似的事儿。要是我的同胞,会以开酒吧的名义把它拖回来,再经过逆向开发最终使其能承受起降。可俄罗斯在这方面很像她曾经的死对头德意志,还老实巴交地为它在碎石上铺一小段铁轨。
少年保尔•柯察金背着小包袱爬上黑白片里的货运列车,头发被烟囱冒出的滚滚煤烟吹飞起来。
就连垮掉的克鲁亚克无票扒车后也证实车头是朝前的。

从比我们家厨房还小的包厢里出来,呆立在莫斯科站月台上,外面宏大的景象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不愿意破壳而出,硬是被砸蛋女一锤子轰出来的那只背着行囊的晚熟的鸡。
这感觉久久挥之不去,直到站前广场空中忽然飘出两个字儿,准确的说是一堆“2”字气球腾空而起。我这才醒过焖儿来仰天大笑,老婆也跟着乐了。我们想别人6个小时的行程我们能抻成六整天,这反常的情怀应该是够在半空中认领一个二的。

乌鲁木齐有乌鲁木齐河,北京有筒子河,这些都像可以上盖儿的水渠。西化的外滩与租借过的海河两岸又少有中式建筑。
我觉得莫斯科河比泰晤士河美,景色没有遮挡,呼吸也不困难,那是因为看泰晤士河的时候我正钻进充气大玩具里打工。



满血复活的双头鹰捍卫着流血牺牲的五角星,不灭的圣火以瞬息万变的姿态显灵。

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品,艺术品柜台里倒不知摆的是什么。

买双鞋,然后相跟着打磨这岁月之痕。

过了路口没走多远,父亲和他脖子上的儿子向右拐进了一座东正教堂,母亲拉着女儿继续走,小姑娘的双肩背里只装着她的毛绒熊。


前一日在街上闲逛,发现警察在很多街道布置警戒线,有的路口干脆被两辆重型卡车交尾式封堵,大有要和北约展开巷战之势。第二天搞明白了,看了会儿体态健硕的俄罗斯人闷闷不乐、无人喝彩的奔跑,我动身前往离北约很近的圣彼得堡。

苏联消失以后,还有一些名字也跟着消失了,比如列宁格勒。
沙皇彼得大帝在三百年前的沼泽上兴建了这座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开凿出连通大涅瓦河的一条条运河,运来了木料、石材以及意大利、法国工匠。
当这座欧洲北方的威尼斯拔地而起以后,俄罗斯以南不管是贵族还是打倒贵族的新贵,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评价,你就是造的再恢弘,那也是仿的。
走在圣彼得堡涅夫斯基大街上,你可以认出大量中老年同胞外的印度人、韩国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以及前华约国家人,政治意义上的西欧人依然很少。

感谢大牧首心目中的上帝,据说晴天比阴天少的这座城市,在我们居住的这四天里云开雾散。
战斗民族的车速确实快,弯道中租车老兄可以看着反光镜不减速地跟我聊天。然而这条车龙一旦发现行人有横穿马路的意思,不管是不是人行横道,都会一辆一辆逐渐停下来,这一点我们的几个爱讲路权的直辖市经常不能做到。英国一位议员把普京的俄罗斯直呼为蛮族,他的国家也一样做不到,我见识过。
如果你希望和平,就不要随便和一个民族战斗。


众多的聆听者们放下手中的手机、相机,把掌声拍得异常洁净、悦耳,这不只是殿堂造成的效果。楼梯恢复了脚步的流动,几个女孩也开始了她们的参观。
这里毕竟不是音乐厅,所以在歌声中接打电话无可厚非,但其间频繁的闪光灯拍摄,在这个并不昏暗的场所却很是刺眼。这些出自专业相机的强大光束只能证明持有者还没完全搞懂快门、光圈、感光度之间的关系,只是出门前把一个著名的外壳挂在了脖子上。

在冬宫一角,三位带着女翻译的先生摆布着一名身姿优美的模特和她身后的罗马柱,快门长时间铿锵作响,而他们身后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寂寞地等待着仰望。

我对这样的选择并不反感,我想他们肯定是有身体或其他原因,而最重要的,他们没有拿着更适合街拍的变焦镜头在不乏裸体花岗岩雕塑的宫殿里搞室内人像。

正吃着饭,一推门进来一个老妇人,带着盖住耳朵的毛线帽子,臃肿的冬衣外面罩着一块红围裙,是那位女画家。
她背着破画箱子,拿着板凳、画架子,脸上挂着说实话有些呆滞的笑容,缓慢地穿过餐厅走进后门。后门通卫生间,可能也通其它的地方。老妇人进去后,里面立即传出一个男性的吼叫,中间夹杂着老妇人懦弱的喃喃自语。我不想猜测里面是什么样的情景,拔腿就走。
是俄罗斯画家沦为了乞丐,还是乞丐都具有艺术涵养?只要现实稍微沉重一点,这些学术推测马上就变成了冠冕堂皇絮絮叨叨的文字游戏。


捧着发行量最大的导游书籍亦步亦趋,那就把旅行当成了定向越野。
现在连北京六环外西山根儿的新楼开盘都没有低于4万人民币的,而圣彼得堡4千万卢布可以买到使用面积100平米的,不交房产税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建筑。暴发的人民币与困窘的卢布目前的关系是以一当十。不一定非要买,但您有权自己心算心算。




新娘以及女眷们个个身材修长,小头颅、窄脸颊,光彩照人的晚礼服让我忘了什么叫列宁装。
喜宴从傍晚持续到半夜。当我捻灭最后一个烟蒂,从酒店门外穿过大堂准备就寝时,二层酒吧依然传出混合着香槟与伏特加的宽阔歌喉。这歌声让我心里一惊,以为是那首法西斯德国的纳粹战歌。驻足细听,分辨出是高亢程度有几分相似的前苏联《奉献者之歌》。
6天的火车上我只听提前下载的各时期俄罗斯歌曲。列车员老兄把脑袋伸进包厢第一次对我刮目相看,就是因为列车刚一驶入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就从我的便携音箱里传出《向斯拉夫人告别》。

这是一座用沙皇亲戚宅邸改建的酒店。老话讲“穷家富路”,出门该领略就领略,到点儿该回村儿还回村儿。
再说这电水壶外加泥壶瓷杯子,所谓“远路无轻担”,背着背着就觉着沉了。那又能怎么办呢?中途倒是想过扔两件衣服。我是标准的中国中年人,固执地认为没热茶喝会被冻死。
中国大城市目前时兴号称来自日本的铁壶。等中国再有点钱,会不会大量收购连俄罗斯老百姓都淡忘了的银制老茶炊?俄罗斯的“茶”字也发单音,很像用“沏茶”二字混合而成。


几把曾经被贵族的臀部按压过的椅子斜挎着纤细的黄色绶带,以此婉拒观众的就坐。这招儿要换了其它地方比如那哪儿可能就不好使。
少不更事的时候也曾捧着画夹子盘腿坐在中国美术馆冰凉的,嵌着铜线的大理石地面上对着遥不可及的名作走笔如飞。一位老先生俯下身来看了看,摸摸我的后脑勺走了。我当时心中大喜,认为是受到了鼓励性的关注。后来渐渐明白了,那抚摸应该是一种怜悯,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弹得一手好钢琴却发现自己没有绝对辨音能力一样,我也早知道这辈子成不了画家了。不过没关系,观看本身也是一种需要反复磨炼的,不简单的修养。

游船顺着大涅瓦河入海,在几个幽静的岛屿中穿行,画了一个有很多锯齿的圆圈最终回到了起航的码头,用时两个小时。
船舱很宽敞,里面只有一个年轻的四口之家以及一对母女。吧台后面的咖啡机是那种带压力的专业设备,咖啡杯、茶杯、玻璃杯应有尽有,就是没服务员。我们选择的夕阳西下到华灯初上是圣彼得堡最美的时段,可游船上的酒水供应竟然处于下班状态。
广播员大姐掐头去尾用超过一个半小时持续进行诗意朗诵,她坐在接近船头的没有光线的角落,面前也没有水杯。大段落的叙述之间她会发出一声轻叹,那里面情绪控制与呼吸调节兼而有之。
龙骨分出的碧波与涟漪般的嗓音平添了口渴的程度。有那么一刻,我放弃了四周的景色,渴望着有一束光线能照亮那个声情并茂的方向。
我渴呀,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句著名的革命论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什么什么。
这一炮就发自阿芙乐尔。
苏联解体后,有思想家才勇敢地站出来放炮,说阿芙乐尔那一炮根本就没响。他还扭头指着中国说邱少云趴在不是人的燃烧弹下面一动不动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说董存瑞手举炸药包高呼不要相信他的中州班长。前几日就因为唐玄宗没搭理他,他话锋一转断定杨贵妃其实没那么胖。
我的没头没脑只剩下虫吃牙的大微思想家啊,你口腔中的溶洞怎么就这样欲壑难平?小地方儿光脚出身二三十年前的高考状元,粗茶淡饭竹林茅舍养不活你了是吧?

我挑了几把有族徽纹样的老勺,准备回去送给朋友当家伙事儿。
临走时发现门边儿上孤零零插着一张硬板儿旧照片,里面那位年轻女子让我想起旧俄国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她混在杂物堆里非常无助,我便握着她走到老板面前,老板比划一百卢布合十块人民币,又额外做了个手势让我千万别再讲价了,之后我把她夹进我的笔记本里。
我无意把她放在这里展示,只是不忍心她被一次次转手,到我这里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的右手握着一支鹅毛笔,我的右手夹着一支香烟。他用左手捂住胸口,那是雕塑师在向食客暗示1837年那场致命的决斗。普希金的诗歌曾经帮助我在那久远的青春期萌生出不少梦想,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位可以参透命运的梦想家。在《梦想家》中他说:
我的晚年将十分平静,死亡这和善的使者来临,叩门低声说该去幽灵的住所了。就这样,在冬天的傍晚,一个甜梦走进安静的前厅,头戴罂粟花编织的花冠,拄着一根慵懒的拐杖……
在写出这首《梦想家》之后没多少年,一颗噩梦般的铅制罂粟绕开花冠与拐杖,植入38岁的诗人躯体。
我又看了一眼普希金的左手,他的左手捂住胸口,我的左手目前还不知放在何处。
回到餐桌用餐巾遮住我的膝盖,古装服务员把两个盖着钢罩的大盘分别摆在我和我妻子面前,又繁琐地向我们一一核对了蒙在鼓里的鱼肉、牛肉摆放位置是否正确,之后猛然将两个罩子像打镲一样高高举过头顶。这和普希金有什么关系?
走出餐厅之前,我回身当着服务员的面,向普希金深施一礼。

事情没那么玄乎。列车驶入边境城市后贝加尔斯克后,因为两国轨道宽窄问题要对车辆调整几个小时。
在车站附近唯一的一条大街上闲逛,走到摆摊老兄身边走累了,就一边欣赏他摆在墙垛子上的果酱、酸黄瓜、新鲜蔬菜一边手嘴并用地跟他闲聊。
“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哈勒硕。”“你中国人?”“中国人。”“北京?”“北京。”“嗯,北京哈勒硕。”
老兄因为猜对了显得很高兴。我递过一根烟给老兄点上,他吸了口烟背出一串中国地名,其中我能确认的有吉林、“哈了宾”。我指指刚才和他说话的老大姐问是不是老伴儿,他摆手,指着马路正对面的楼房说他住这里,指着斜对面那栋说她住那里,两栋楼房的样貌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抗震楼强不了多少,然后我老婆就跟上来了。
接过花老婆要掏兜儿,老兄不让。出于礼貌,我们也选了两样能生吃的青菜并拒绝找钱。
何成想这菜简直太好吃了,我在村里6年都没种出过酸口儿的绿叶菜。下了火车我就莫斯科彼得堡到处寻觅,这俩字儿北京话念学么。未果,深感当初的礼貌太不大方。

夜色中一位年轻母亲拉着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从酒店门口经过,小女孩看着门前花盆里类似绣球的鲜红花簇就不走了,伸手抓住了其中一朵。
母亲终于感觉到了阻力,她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小女孩手里牵着半盆连枝带泥的花朵已经跟着她们走出了好几步。
母亲拉着小女孩走回来,一边把花栽回花盆,一边低声埋怨着孩子。小女孩可能没有听见她妈妈说什么,因为她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朵刚刚还拿在手里的花。
我按灭烟头走过去,把那朵注定属于她的花摘下来,躬身献给了小女孩。
神奇的一幕在女孩眼前发生了,那朵花正向她靠近,然后扑进她的手里,这一切都很符合她知道的那些童话的逻辑。她抬头咧开豁着好几颗牙的漂亮小嘴儿乐了,母亲也冲我笑了笑,小声冲孩子嘀咕了一句,之后我得到了一声稚嫩的俄语道谢。母女俩走出我视线前,好几次那张漂亮小嘴转过来冲我咧着。
我不可能用相机记录下自己作为男猪脚的一幕。空口无凭,上一幅焦点不在花身上的庸俗的小布尔乔亚照片为证。

在堤岸边,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外景。正式拍摄前,新娘把充当司机的公公招呼过来,挽着两个男人的胳膊乖巧地先来了几张合影。
他们附近停着一辆普通的日本进口轿车,新娘披在婚纱外面的大衣也并不光鲜亮丽,甚至连那位女摄影师也很像是她找来的闺蜜。没有化妆师,没有助理,没有反光板,没有这些,竟然照样可以记录幸福。
在俄罗斯两座最著名的城市,富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而穷人却很难辨认,因为我所见到的人们都难能可贵地讲求着整洁。

我们谁也逃脱不了或早或晚的,命中注定的动荡,我们只是希望在人生的旅游大巴驶入终点之前,能亲自挑几个小站下车歇会儿。
本游记著作权归@8097021185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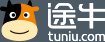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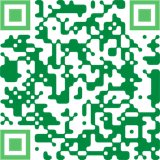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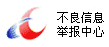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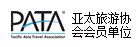
发表评论